2020年12月24日,國藥中生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Vero)上市申請正式獲得NMPA受理。世界的另一邊,輝瑞/BioNTech和Moderna的兩款新冠疫苗(mRNA)也先后獲得FDA的緊急使用授權(EUA)。中美兩國新冠疫苗研發的領跑者們已經撞線,所用時間
2020年12月24日,國藥中生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Vero)上市申請正式獲得NMPA受理。世界的另一邊,輝瑞/BioNTech和Moderna的兩款新冠疫苗(mRNA)也先后獲得FDA的緊急使用授權(EUA)。中美兩國新冠疫苗研發的領跑者們已經撞線,所用時間還不滿一年。
這前所未有速度是如何達成的?近期,美國《連線》(wired)雜志對話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疫苗研究中心(VRC)主任講述新冠疫苗背后的故事。我們編譯了其中部分內容來呈現美國“Operation Warp Speed”(“曲速行動”,美國加速研制和生產新冠疫苗的政府資助計劃)下企業選擇、國家力量、社會責任之間是如何實現平衡并共同完成新冠疫苗研發的。
疫苗正在給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帶來曙光。
而這背后是驚人的科學技術成就:在美國,從新病毒到新疫苗大約只用了12個月,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并且應用了最新的疫苗技術。
《連線》認為功勞離不開美國各地的研究合作者們在研究冠狀病毒上花費數年時間所做的努力,其中一份來自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疫苗研究中心(VRC)主任約翰·馬斯科拉(John Mascola)的實驗室。
正是馬斯科拉的VRC將mRNA帶到了Moderna。他和VRC的同事正確地預見了即將到來的事情,并知道如何為此做好準備。
“沒有人知道下一次疫情會是什么。它可能是流感的變種,也有可能是多種病原體之一。不過有個簡單的辦法,你可以去看看過去20年爆發的疫情清單。如果上面有兩種病毒屬于冠狀病毒家族,那么對它再次出現你大可不必感到震驚。SARS在2002年,MERS在2012年,在疫病大流行史上這是一個很短的時間范圍”,馬斯科拉說。
如今的成果令馬斯科拉感到欣慰,“我們一直相信DNA和RNA這些新技術可以在疫苗學和應對疫病大流行中發揮重要作用。很高興看到這成為現實。”
至于為什么會與在當時名不見經傳的Moderna合作,馬斯科拉表示,這得益于雙方的互信基礎,“我們相信Moderna有非常強大的科研能力來制造RNA疫苗”。而這一基礎的獲得,更多是來自雙方從2017年開始的針對塞卡病毒的合作和對冠狀病毒等傳染病疫苗研究上的共同興趣。
馬斯科拉坦誠其中的運氣成分。“對于原始的SARS和MERS我們都能成功通過刺突蛋白(spike protein)來制作疫苗,所以我們有信心。但也并不確信當另一種冠狀病毒來襲時我們是否可以應用相同的結構來穩定突變。我們只能試著觀察病毒和刺突蛋白的遺傳序列,將我們最初對SARS所做的工作轉移到新的SARS-CoV-2中去。結果是,在這些突變中立即起了作用,這讓我們在比賽中取得了領先。”但最核心的還是基于對冠狀病毒的研究積累。
“我們確實很幸運,但慎重來講,我們對冠狀病毒也足夠了解。”
以下對話的節選:
Q:早在COVID-19出現之前你就提倡基于mRNA開發新疫苗和新的制造方法,最近的幾周你是否感到得到了某種證明?
馬斯科拉:結果的確讓人欣慰。不僅僅是證明,我們一直相信DNA和RNA這些新技術可以在疫苗學和應對疫病大流行中發揮重要作用。很高興看到這成為現實。
Q:VRC在mRNA和刺突蛋白上的研究最終是如何由一家相對較小且缺乏經驗的制藥公司Moderna來進行開發的?
馬斯科拉:我們之間的合作關系在2017年或者更早對塞卡病毒開展研究時就開始了,在傳染病疫苗上強烈的共同興趣讓我們之間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系。Moderna對寨卡病毒的研究很感興趣,他們從美國生物醫學高級研究和發展管理局(BARDA)拿到一些資助,并且希望找一個科學合作伙伴來進行疫苗的設計。而當時VRC也考察了許多有能力生產RNA疫苗的公司,我們相信Moderna有非常強大的科研能力來制造RNA疫苗。之后在共同探討其他感興趣的領域時,我們提出冠狀病毒或許會是一個富有成果的領域。
Q:我想這不單純是“猜測”更是基于一個好的“假設”對嗎?也就是說,冠狀病毒將成為一個問題。
馬斯科拉::我們其實做了兩手準備。沒有人知道下一次疫情會是什么。它可能是流感的變種,也有可能是多種病原體之一。不過簡單的辦法,你可以去看看過去20年爆發的疫情清單。如果上面有兩種病毒屬于冠狀病毒家族,那么對它再次出現你大可不必感到震驚。SARS在2002年,MERS在2012年,在大流行史上這是一個很短的時間范圍。
我們與Moderna一起設計了MERS的早期臨床前疫苗,因此能夠測試我們的mRNA是如何工作的,并且有能力對RNA帶給人體的免疫反應進行一些設計測試。當發現COVID-19病毒是冠狀病毒時我們已經奠定了很多基礎。
Q:但你是否擔心在MERS上刺突蛋白的研究無法應用到COVID-19病毒或SARS-CoV-2上?
馬斯科拉:對于原始的SARS和MERS我們都能成功通過刺突蛋白來制作疫苗,所以我們有信心。但也并不確信當另一種冠狀病毒來襲時我們是否可以應用相同的結構來穩定突變。我們只能試著觀察病毒和刺突蛋白的遺傳序列,將我們最初對SARS所做的工作轉移到新的SARS-CoV-2中去。結果是,在這些突變中立即起了作用,這讓我們在比賽中取得了領先。
Q:所以,這其中有運氣成分。
我們確實很幸運,但慎重來講,我們對冠狀病毒也足夠了解。
現實是科學界為刺突蛋白所做的第一個設計就成功了。不過讓我們來做個假設,如果我們做了一個疫苗但效果不是很好會發生什么?我們可能不得不回去做第二代設計,為此將損失三到四個月。想想看那時世界將會怎樣。塞卡病毒便是如此。VRC與Moderna一起設計了兩種類似蛋白的設計(不是刺突蛋白,而是病毒表面的蛋白),第一款臨床效果不太好,沒有誘發非常好的免疫反應,直到第二個才做到。這在科學界很普遍。
Q:為什么會有“Operation Warp Speed”疫苗資助計劃?它的任務似乎是VRC應該做的?
馬斯科拉:其中有一個重要的不同。我當時贊成創立資助計劃,正因為我是疫苗中心的負責人,我清楚我們可以做什么和自己的局限。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有能力開發一款疫苗并且進行早期臨床,但沒辦法將其商業化或大規模生產。NIH不像BARDA那樣資助后期研發,需要找到私營公司來進行合作。此外,我們中的很多人已經在政府工作多年,此前也曾見過傳染病疫情肆虐,因此很清楚當遭遇這樣一個嚴重疫情時政府內部應該把資源整合在一起來共同應對。
Q:但是為什么要從企業而不是政府或學術界找一個主導者呢?
馬斯科拉:我們中的很多人都建議找一個外部顧問。當你引入Big Pharma 的人來運作項目時你就能得到他們的意見,這對公眾來說是一種增值。我在VRC與企業打交道的經驗是,如果你想和企業合作就需要了解他們的動機。我是一位政府研究人員,我理解自己的動機。輝瑞表示不與我們合作決定自己做。Moderna 與我們合作的動機是什么?如果每個人都這么說怎么辦?這才是我思考的問題。
Q:你曾表示不同藥企進行的新冠疫苗臨床試驗和收集到的數據應該進行統一。在我看來現在這并沒實現。各個藥企的實驗不僅有不同的臨床終點而且都沒有進行頭對頭試驗。藥企更愿意自己推進實驗而不依靠獨立的第三方研究人員。您對此是否有信心?
馬斯科拉:關于這一點已經進行了大量討論。正如你所知道的,如果資助的實體是BARDA,通常來說BARDA會以更傳統的方式提供資金:按照合約提供資幫助企業開發疫苗,同時要求企業報告進展和里程碑。這種情況下,每個公司都做自己的事情并不需要協作。
另一種方式是一切都由政府控制,每個公司按方案分配任務。這種被稱作母方案(master protocol)模式此前也曾被廣泛討論過了,在某些情形下這也不失為一個好主意。
不過對于新冠病毒而言這些都很難實現。首先,疫苗問世的時間點不同,所以永遠無法真正實現頭對頭的試驗。因為傳染病不斷變化至關重要的對照組也不斷變化。第二,疫苗試驗規模巨大,比任何一個實體所能協調的規模都要大。第三,由于疫苗商業化向FDA提交上市許可所需的數據必須通過一家公司來進行申請。因此從速度和效率的角度讓FDA認可的一家公司作為試驗的責任主體更好。
不過“曲速行動”對試驗也提出了一套嚴格的要求。他并非一個母方案而是一系列所謂的協調方案。它們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如果您退后一步看到它們的設計都非常相似。監管方即由NIH創立的數據安全監測委員會(DSMB)對計劃中的每個試驗一視同仁。這些協調都是我們所推進的。
Q:但是輝瑞并沒有得到warp speed的資助,所以他們有著不一樣的DSMB。這會不會為之后的批準和對比帶來問題。
馬斯科拉:有件我想你已經知道的事非常重要。即使是由“曲速行動”資助的公司,他們的疫苗在提交上市許可或EUA時都會提交給FDA審批。VRC不會扮演FDA角色。
另外我想說的是,輝瑞始終與“曲速行動”保持了緊密聯系。我感覺他們正在做的試驗與Moderna的試驗十分相似這也將使申請變得更加容易。答案的另一部分是,除了輝瑞參與數據安全監測委員會的其他公司還會貢獻他們的數據。因此,我們可以一起查看所有試驗的數據。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將這些試驗結合起來我們將可能從中會學到很多東西,而不是一個個單獨的試驗。
Q:僅有三期數據就可以做到這些嗎?就算輝瑞和Moderna并沒有定期測試那些無癥狀的人?他們有在收集你所需的數據嗎,還是需要等到疫苗上市后?
馬斯科拉:不,三期試驗還在進行中。輝瑞和阿斯利康都在收集大量關于所謂“病例”的樣本和信息。而每個參加試驗的感染者將成為一個病例。這些詳細的實驗室數據和醫學信息都是三期試驗記錄的一部分。
Q:但是那些非感染者的信息呢?
馬斯科拉:為此我們會進行一些相關研究,在其中詳細研究病例和非病例(已接種疫苗但未成為病例的),以比較他們的免疫反應。以便了解免疫的相關性,每項研究都是如此設計的,這也是被所有公司認可的。
Q:疫苗進入更廣泛的人群之后將會發生什么?是否會針對長期安全問題或免疫持續效力來進行跟蹤?
馬斯科拉:我認為這是可行的,FDA的確會在產品上市后進行監測。而且EUA并非上市許可,產品在獲得正式許可之前都會受到監測,公司也將有責任在履行其EUA時進行詳細的跟進。
Q:拋開疫苗專家的身份,你想看到哪些數據?想知道關于新疫苗的什么信息?
馬斯科拉:其中有很多關鍵數據。總的來說,我們知道疫苗在預防有癥狀的新冠病毒方面非常有效。多數人只有在夢中才敢設想94%或95%的療效,這意味著病毒容易受到免疫系統的影響,我們終將控制疫情。
但是我們并不知道所有事情。我們不清楚疫苗在老年人群或體弱多病的老年人、或者免疫系統不完善的人群中的效果如何。我們不知道免疫能夠持續的時間,會是一年還是兩年?我們不知道無癥狀感染這是否可能被預防。我們還有很多東西要去學習,第一批研究是學習它的關鍵時機。
最后,我們真正想知道的是免疫的相關性,它是免疫系統的關鍵參數和保護機制。免疫系統總是協同工作的,因此通常當我們識別某些關鍵參數并提升它可以為我們帶來保護。
Q:你是否擔心正在和將要進行的疫苗臨床試驗所帶來的影響?一款疫苗已經奏效但仍要繼續進行試驗時,那些對照組的志愿者們將會怎樣?
馬斯科拉:我認為這是一個好問題。我們擁有了遠超預期的疫苗,也意味著我們可以去棄考這樣的倫理問題:當你的疫苗已經取得不錯的臨床證據,隨機對照試驗還應該進行多久?怎樣確認這是否是好證據呢?
我覺得并非是某個公司的新聞稿來決定的,而是FDA看到數據并表示“我們看過主要試驗數據了,的確有95%的有效性。”并且FDA批準緊急使用授權。然后我們可以提出這個問題:我們什么時候將疫苗提供給研究的安慰劑治療人群?我認為這將是未來幾周FDA疫苗及相關生物產品咨詢委員會(VRBPAC)會討論部分。
Q:你已經見證了過去一年疫苗開發的進程,其中又有怎樣的啟示?不只是對于疫情大流行還包括一般的傳染病。
馬斯科拉:回頭看當初在用新技術來研發疫苗時會有各種擔憂。現在我們已經我們已經證實mRNA疫苗可以起作用并且可以迅速投入使用。我認為腺病毒技術也可能提供相當好的保護,這些新技術很可能也是可行的。
另一點讓人感到鼓舞的是這證明了基于科學結構的疫苗設計是可行的。同樣的概念也開始針對呼吸道病毒等其他情形進行測試了。
現在我們需要一個更好的全球監測體系。這套體系可以使用現代技術進行測試讓我們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我們還需要更好的全球臨床能力來推進大規模的試驗。美國政府可以提供100億美元、120億美元來激勵藥企,但是世界其他地方呢?我們如何搭建臨床試驗所需的基礎設施?
Q:人們都在說我們用了一年時間就得到了新冠疫苗,但我知道這并不準確。我們花了近二十年才真正了解冠狀病毒。但如果下一場疫情不是冠狀病毒呢?
馬斯科拉:病毒的確可能會從那些我們沒有做好準備的病毒家族中出現。我們知道世界上大約有20個主要的感染人類的病毒家族,在過去50多年甚至更長時間里,幾乎每一次爆發的疫情都來自這20個病毒家族之一。如果我們齊心協力對每個病毒家族進行詳細研究、制作疫苗,像我們對冠狀病毒所做的一樣會怎樣呢?我們應該制作一些原型,那么就算出現該家族的表親,一種我們從未見過的病毒,至少我們已經為疫苗設計奠定了基礎。之前人們會認為這是一筆很大錢,但在經歷過大流行之后現在這已經算是一筆小投資了。
Q:你是指如果一場疫情要花費16萬億?
馬斯科拉:正是這樣。我不想拿出一些并不完全準確的數據,不過每個病毒家族只需花費2000萬美元,就可以制作一個原型疫苗并在進行臨床測試。五年十億的投入在過去會被認為站不住腳。但如今如果能為下場大流行做好準備,這很可能是一個非常好的投資。
本文來源:E藥經理人 作者:蘇唐 免責聲明:該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僅代表作者觀點,轉載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并不代表“醫藥行”認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涉及作品內容、版權和其他問題,請在30日內與我們聯系
 客服微v信:
客服微v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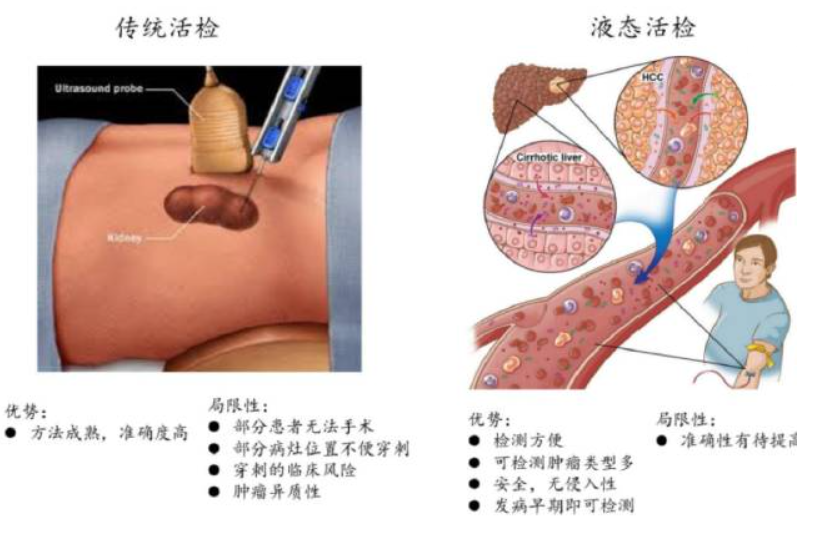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31568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31568號

